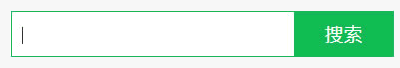我怎么在哭。
耳边飘荡着很多糅合在一起的人声,焦急的、担忧的、害怕的。
他们好像在说,年年,年年。
我睁开疲惫的双眼,眼前晃过数张模糊的人脸。
“醒了醒了。”
有人欣喜喊道。
我在哪,他们是谁?
待我看清眼前时,我慌了,几个穿着骑服的陌生男女围着我,我害怕的往后腾挪,手腕却传来撕裂般的疼痛。
疼痛,好像很多年都不曾感觉过了,痛的我的眼泪都流了下来。
“年年。”
其中一个男子见我身子一歪要倒,连忙拉住我。
我的头尤自钝痛着,什么也想不起来,我好像只记得我死了,在乱葬岗飘啊飘,好像还遇到了一个叫仲春的书生。
“你们是谁?”我蜷缩着身体,害怕的看着他们。
“年年,我是景赫啊,他是晏思齐,我们是最好的朋友,你不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。”
那个自称叫景赫的男子便是刚才拉我那一个,他的眼中溢满了担忧,手足无措的望着那个叫晏思齐的男子。
晏思齐蹲下身为我把脉,又问我伤了哪里,我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,他怔怔看我一眼,似乎在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失忆了。
晏思齐明显比这几个年轻人都镇定的多,我的心像是被悬在了高空一样揪着,目光不安的扫视在众人的脸上。
“我是谁?”
我是安国公的嫡孙女,江年年。
名字是我祖父取的,花开年年,花似年年,他希望我长命百岁,一生顺遂。
我祖父有两位挚友,一是晏思齐的祖父晏怀,一是景赫的父亲景知尘,前者是定国大将军,后者是当朝丞相,陛下曾说,武晏文景可安天下,这是天意。
景晏各取一字,不正是京安么。
我们三人都在御风书院读书,今天是书院秋狩比赛的日子,我的马突然不知怎么惊了,不等他们反应过来,就已经驮着我横冲直撞的朝山里去了。
幸而当时有洛桑临危不惧追了上来,见无法安抚惊马,她冒险抓住我抛的缰绳跳到我的马上,一刀贯穿了惊马的脖子。
果然是关外来的女子,真是飒爽果断。
“没关系的,回去好好调理调理,一定会想起来的。”
景赫安慰我道。
晏思齐张了张嘴,但是好像该说的话都被景赫说了,一时也想不到说什么,只得作罢。
我看到了坐在另一棵树下的洛桑,她咬紧着牙关,手肘的伤口深可见骨,不断有鲜血涌出,绯红色骑服布满了暗沉的血迹。
我的头还是在钝钝的痛,我推了推身侧的景赫,叫他赶紧过去帮洛桑处理下伤口,再这么下去,她的血都要流干了。
景赫不大情愿的推了推晏思齐,使了个眼色,“你去吧,你不是在军营里和军医学过吗?”
晏思齐没做太多考虑,转身过去了。
这场秋狩因为我出了意外被迫中止,回家后我吃了很久的药,但是还是想不起来之前的事。
我爹娘急的摩拳擦掌,恨不得遍寻天下神医,祖父倒很淡定,只不过是失忆而已,又不是傻了,有什么关系。
病好后,我照旧去书院读书。
只是乍一进门,就瞧见几个鬼鬼祟祟的女同学挤在一起,正在往最后一排的书桌上倒什么东西。
她们竟然在刷浆糊,书和纸都被牢牢的粘在了桌面上,估计是等着看这张书桌的主人出洋相。
“你们在做什么。”
我喝止道。
一人抬眼一看,心虚的扯着其他几人作势就溜,我刚追几步,却见洛桑走了进来,她在桌旁呆呆的立了片刻,像是对此早已麻木。
“洛桑。”我连忙叫住她。
她看着我,挤出一个无奈的微笑,“是江小姐啊。”
“你叫我年年就好。”兴许因为她救了我一命,我看见她就觉得分外的亲切,“你不要坐这里了,坐我旁边去吧。”
洛桑轻轻的摇了摇头,“不用了,坐哪里最后都一样。”
编辑:iihuo68 来源:心有桃源:年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