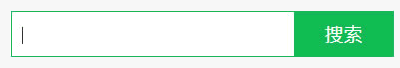第五章侧妃
那位姑娘是他求娶来的,满京城都知晓。
她是镇北将军的女儿,从小在边境长大,连名字都与众不同。
她叫张月,意为边关永平之意。
她上过阵杀过敌,玩得一手好蹴鞠,一回京城就引起一阵轰动。
我自小长在宫里,对这些也有些新奇。如果不是她即将嫁给我夫君的话,我可能会厚着脸皮去拜访她,听听那些从未见过的风景。
可是她即将是我夫君的侧妃。
我接了宫里来的旨,把自己关在房里,一关就是三日。
家中大小事我一并丢了开,并且谁也不见。
这几日里,我想起爹爹,还有我从未见过面的娘亲。
娘亲去得早,爹爹是男子,我自幼时起便得他十分疼爱,可他却从未教过我何为情爱,更未曾传授我识人之道。
不怪我父亲,他少年丧妻,他半生忙碌,大半心力都奉献给了天子,只由得女儿在深宫与皇子公主一处长大。
我在太后娘娘身边待了那么多年,只听她说女儿家到了好年纪,是要寻个好夫婿成婚的。婚后也当大度贤良,相夫教子。
想想我这些年,肚里确实有不少文墨,却在情爱一事上懵懂至今。年少时心动,又门当户对,于是许了终生,同这朝野间其他的世家贵女一般告别高堂,一头扎进夫家的宅院,协理家务,孝顺长辈。
我从前只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,即使短暂迷茫过,仍然觉得这就是我的命。
诚如赵誉从前所说,我大概是读书坏了脑子。
可是这次不知怎的,我这榆木脑袋好似开了窍,竟然觉得这一切陌生起来。我前面十几年的人生仿佛是提线木偶一般,看似处处自己做主,可又处处只为了合别人的意。
但是我仍旧理不出什么头绪来,院墙内的日子过分单调,我就如同笼中困雀,实在想象不出另一番天地是何模样。
这三日里,赵誉没有来找我,太后娘娘倒是派人来请好几回,我抱病不出。
我日日在房里枯坐,婢女袅袅急得哭了好几回。
我们自小一道长大,此时她倒似比我更伤心:[姑娘,我们回金陵去吧,何必要在这里受这种鸟气。呸,还有脸让你筹备婚礼,也不看看当初是谁求来的婚事。]
是啊,当初是谁求来的婚事?
我竟有些不想记起来了。
我摸摸她的头,让她不要生气。
第四日,我打开门,叫来管家,吩咐他去采买一应婚礼所需。
我与他道:
[我也是第一次筹备婚礼,经验不足,一应事宜还要多劳烦你。]
他膝盖一屈,跪在我面前道:
[娘娘,王爷吩咐过了,按正妃的规制来。]
我怔住了。
管家的脊背更加弯下去。
可能也是怜悯我,才一开始就叫我知晓。
我不为难他,把他打发走之后,穿上正妃服制进了宫。
赵誉不在府里,果然在自己母后宫里。
只是同在的还有那位红衣少女。
我走进殿里时,她正翘着二郎腿喝着花茶,隔着一张茶桌与赵誉笑作一团。
见我进来,她将我从头到尾打量一圈,嘴里啧啧称奇:[好一个美人,赵誉你小子艳福不浅啊。]
转头又嘟囔道:[穿那么繁复,这种天也不嫌热。]
我有些难堪,却直往太后那里行礼,一眼也不看赵誉。
我没等太后询问,便先开口道:
[母后,王爷怎么回来也不知道遣人说一声?我这几日病了,还不知晓王爷早回了呢。]
[只是也不知晓谁传的话,竟说王爷求娶了个侧妃,还是将军之女。您说,这是不是无稽之谈?]
我爹爹后宅干净,我在家只管饮茶作画,哪里像这样说过话。
在听见自己说了什么的那一刻起,我就觉得悲哀。
她一脸尴尬,还没来得及回话,下首的男子腾地站起来,声音是黄沙磨练过的微微沙哑:[当然不是无稽之谈,是本王主动求娶。]
我不自觉开始发抖,有些站不住。
天旋地转,殿中安静得出奇。
这时那姑娘嗤笑一声,道:
[京城的金枝玉叶们竟接受不了三妻四妾?也是奇了,原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此简单的么。]
我自制不住就要跌到地上之时,那个男人冲过来接住了我,将我抱往侧殿去。
无人接那姑娘的话,她毫不在意,反继续与太后攀谈起来。
我眼前发晕,被殿中又响起来的欢声笑语吵得头疼。
抱着我的男人凑近我耳边,让我等一等,最多两年就好,他不会碰她的,一切就如同从前一般,什么也不会改变。
我用虚弱的气音质问道:[从前是哪般?你又为何娶我?]
我连续几日没好好用饭,已经没有力气继续问他,让我等什么,凭什么让我等。
他也没有解释,我只记住了那个[两年],便在侧殿的床上昏睡过去。
我醒来之后,虽不再管迎亲事宜,却也默认了,如这都城之中所有名门贵妇一般大度贤淑。
赵誉时时强调,说他虽然主动求娶,但是并不会弄假成真,只是做个样子。
我信他。
即使全京城都知道,誉王爷在边境对镇北将军之女张月一见钟情,遂主动求娶。
我这个成亲三年无所出的发妻是个贤良之人,成全了一段佳话。
我也信他那时说的是真的。
即使不与我解释任何细节,我也信他。除了信他,我已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。
编辑:iihuo68 来源:遥相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