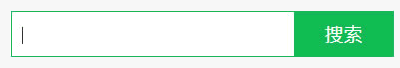1
我是大清最后的格格。
所有人都在这个时代向前走,只有我被困在后宅之中,做一个格格。
后来我遇见了一个人,他告诉我,想踏出这道门很容易。
我故步自封,不敢踏出那一步。
因为我是最后的格格。
直到他战死的消息传了回来。
直到我已经家破人亡。
我看着那道门槛,终于走了出去。
[1]
我十岁那一年,大清亡了。
爹爹喝得醉醺醺,抱着我哭了一晚上,嘴里一直叫着皇上。
好像没有了皇上,他就丢了半条命一样。
我爹是个不太受重视的郡王,和当今皇上有着一点微薄的血缘,因而就算他一辈子碌碌无为,但依旧能受人尊敬,衣食无忧。
可以说,只要我爹安分守己,不去做什么掉脑袋的蠢事,可保他一辈子荣华富贵,做个闲散王爷。
现在这些都没了。
皇上被迫退位,大清亡了。
我爹这个郡王和我这个格格,成了过去的产物,地位尴尬。
可我爹好像不认命,他整天做着光复大清的美梦,一向不喜与人交际的他竟然主动邀请一些有权势的客人到府上。
有名人商贾,也有军阀地主。
我当时很小,只记得家里许久没来过那么多人,我心里没由来产生对未知的恐惧,整日里将自己关在屋子里,不敢踏出门一步。
我爹将王府里的一切都保持得像大清没亡时一样。
仿佛这样,就能当做什么都没变,他还是那个尊贵的王爷。
我爹依旧按照格格的标准来教导我,府上的丫鬟婆子见到我都会福身行礼。
[格格吉祥。]
就这样,我长到了十七岁。
[格格,您院子里的杜鹃开了!]
丫鬟如意蹦蹦跳跳地跑到我面前,福了福身子行礼,然后惊喜地告诉我这个消息。
如意今年十三岁,八岁那年被卖进了府里。
她和其他的丫鬟不一样,她的好奇心非常旺盛,也很向往外面的世界。
每次听到了什么新奇的事,比如哪里又打仗了,哪里又闹革命了,都会兴冲冲跑来和我说。
我每次都会耐心地听她讲完,但不会发表意见,如意也总是像倒豆子一样向我倾诉,并不在意我的看法。
我放下手中的绣品,和她一起去了后院。
我种的那些杜鹃开得很好,花团锦簇,异常漂亮。
从小到大,我爹总是将我关在自己的小院,说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不可抛头露面。
我已经习惯了听从他的话,因此并不觉得他这个要求有什么不对。
但终日里待在一处地方总归太过无聊,我便寻了法子打发时间。
杜鹃花的种子是伴我长大的嬷嬷从外面买回来的,为了种花,我翻阅了许多书,甚至连我爹书房的书籍也被我看了一遍。
我爹发现后很不悦。
他觉得女子读太多书,将来夫家会不高兴,为此还责罚了我一顿,让我抄了三遍女戒与女训。
我抄得手腕酸痛,但心里没什么委屈,因为我成功找到了有关种花的方法。
从那之后,我时常把自己关在小院里研究,如意就蹲在门口帮我放风。
每当发现我爹朝我的院子走来,她就会故意发出一些声响,我就会匆忙放下沾满泥土的铲子跑回屋子洗手。
若是让我爹发现我如此不顾形象,怕是又要挨罚。
我站在屋檐下,看着院子里的杜鹃,嘴角微微上扬,心里有一种满足感。
[格格,你好厉害啊!这些杜鹃开的比外面花店卖的漂亮多了。]
如意在花丛中跳来跳去,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崇拜。
我抿着唇,眼底全是笑意。
我让如意采了一些杜鹃花瓣,特地选了那些开得最好,颜色最鲜艳的,晾干之后可以做蔻丹。
如意在我身边好奇地问:[格格,你怎么什么都会啊?]
我一边摘花瓣一边回她:[怎么可能什么都会,我不会的可多了。]
[那格格你不会什么?]
[不会赚钱做生意,不会扛枪打仗,男子会做的我都不会。]
[可是外面的那些女子,有人会赚钱做生意,有人也会扛枪打仗,男子能做的她们都能做,甚至比男子做得更出色啊。]
像以往一样,如意又提起了外面的世界,之前我已经从她的口中得知了外界发生的变化,知道外面已经变成了我无法想象的样子。
但是这次,我却沉默了。
许久,我抿了抿唇,说:[我和她们不一样,我是格格。]
如意嘟囔:[对哦,您是格格,怎么能做那些事?]
格格,从前象征着尊贵的地位。
如今,我竟然不知这是一种荣耀,还是枷锁。
我几不可闻地叹息一声,不去想这些。
抬头看了看天,阳光正好,我让如意搬来了藤椅,放在院子中央。
我躺在藤椅上,周围是杜鹃花海,风一吹,周围便盈满了花香。
忽然,院门被人敲响,我睁开眼,看见我爹身边的贴身小厮走近,向我行了个礼,恭敬地道:[格格吉祥。]
[格格,王爷说今晚他要在前院宴请客人,让您待在院子里千万别出去,若是让外人冲撞了可不好。]
我点点头,挥手让他下去,没有多少意外。
我爹隔一段时间都会请些人来府上做客,短则几天长则月余,每每这个时候,我都得待在自己的院子里。
不知道这次得多久才能出院门。
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没了好心情,命人撤了藤椅,回屋继续去绣我的刺绣去了。
时间很快过去,如意在屋里点起了油灯,还提醒我:[格格,仔细伤了眼睛]
我抬头看了看窗外,发现天还没黑,便把绣品搬到了外面,坐在廊下继续手上的活计。
突然,一阵风起,卷走了我刚绣好的手绢。
眼看着洁白的手绢被吹走,我连忙起身去追。
追到院门口,我意识到什么,顿住了脚步,踟蹰着不敢出去。
手绢正好落在院门外不远处的地面上,只要迈出去捡起来就好。
但那是条青石铺就的小路,平时人来人往。
我站在那里,呆立不动。
脑海中想起白日里那个小厮的话,今晚府里会有外人,若是出去被人瞧见,到时肯定会被罚。
就在我犹豫之时,有人捡起了那张手绢。
我猛地望去,一名穿着军装大约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拿着那张手绢。
他看见我,先是打量了一瞬,有些惊讶,而后问道:
[这是你的吗?]
[2]
这里是后院,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男人是如何闯入这里的,心底是前所未有的慌乱,不知所措。
那男子见我不回答,走近了几步。
我连忙道:[别过来!]
他顿住脚步,仿佛意识到什么,退回了原地。
[抱歉。]
他似乎觉得吓到我了,抱拳弯腰行了一个极其生疏的礼,配上他那一身整洁的军装,显得滑稽又违和。
[在下裴铭,受邀来府上做客,酒后出来走走,谁知迷路到这里,碰巧捡到了格格的帕子,希望格格宽恕。]
我并不诧异他一语道破我的身份,毕竟王府之内,穿着大清格格服饰的只有我。
我勉强镇定下来,指着他手上的手绢,又指了指门口处的青石板,说:[你放在那里就好了,然后赶紧离开。]
否则,若是让我爹知道了我私下与陌生男子见面,怕是会打死我。
裴铭点点头,按照我的话将手绢放在了石板上,还贴心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压住,免得再次被风吹走。
他看了我一眼,神色有些不好意思,说:[抱歉,我不知道怎么出去,能劳烦格格指个路吗?]
我唤来如意,交代她把人悄悄地带走,不要让其他人看见。
如意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,严肃地点点头,领着裴铭走了。
望着二人远去的背影,一直绷着的弦终于松了下来,我连忙跑到门口,将手绢拿了回来。
和手绢一起拿回来的,是一块包装精致的糕点。
我撕开包装将糕点放入口中,入口即化,甜而不腻,比我在王府里吃到过的更加好吃。
我看了眼包装纸上的字,品芳斋。
很快天就彻底黑了,小厮在院门口挂上了灯笼。
如意小跑进了院子,来到我面前,她四处看了看,用无人能听见的气音小声和我说:[格格,人已经带出去了,我盯了一会儿,他嘴挺严实,没和别人说不该说的。]
我点点头。
[格格,您知道王爷今天宴请的都是些什么人吗?]
如意一脸神秘,我摇了摇头。
[全是军阀!]
她忽然提高了声音,我被惊了一下,随即皱眉。
现在想来,白日里那名年轻男子应该也是我爹这次的座上宾之一。
我的心底泛起了浓浓的担忧。
虽然我从不出门,但也知道如今的世道军阀割据,战乱不断。
我爹在这种时候和军阀们往来密切,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。
不过就算会发生什么,也不是我可以左右的。
原以为今天的相遇只是我人生中一段转瞬即忘是插曲,却没想到不久之后,我竟再次见到了裴铭。
[上次酒后失仪,险些惊扰了格格,今日在下特地来向格格请罪。]
我震惊地望着他,视线缓缓下移,落在他手上提着的两个纸袋子。
[这是品芳斋新出的点心,我想格格应该还没尝过吧?]裴铭笑着问我。
品芳斋,我还记得,是上次我吃过的那块很好吃的糕点。
但是……
[有人看到你在这里吗?]
我很害怕,我怕被说闲话,和一名陌生男子私下见面,这在我过去十几年所受的教育中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
裴铭愣了愣,似乎完全没想到我会这么在意这个。
是啊,若是外面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,便不会连和男子见一面都战战兢兢。
[今日司令和王爷有事要谈,我就跟着过来了,刚才找了个借口离席,应该没人看见我到这边来了。]
虽然他有些意外,可还是一一回答了。
我暗松了一口气,朝旁边的如意使了个眼色,如意上前接过他手上的纸袋。
[谢谢你的糕点,上次的事情我没放在心上,但是你我男女有别,裴先生以后还是别再来后院了,否则让人瞧见,容易说不清。]
裴铭听完,直接笑了:[有什么说不清的,你我又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,这么封建做什么?]
[格格,大清亡了。]
气氛忽然陷入了一阵沉默。
裴铭意识到自己一时嘴快说错了话,有些懊恼:[抱歉,失言。]
他不该在她面前说这些。
不礼貌。
我神色未变:[没关系。]
大清确实亡了,这是事实。
只是我爹还在做着光复大清的美梦而已。
我再次让如意送裴铭离开,只是这次他走之时,似乎欲言又止,想对我说什么,最终还是放弃了。
他走之后,我尝了那些糕点,依旧很好吃,甚至让我生出些贪恋的滋味,好奇外面的其他事物是何样子。
但我知道这是不应该的。
我爹对大清的执念具象化到了我身上。
他强制我保持着格格的体面,吃穿用度一如从前,并且严格禁止我同外界接触,整座王府,宛如与世隔绝一般。
而现在的我,就是被桎梏在后院府宅之中的一只金丝雀而已。
编辑:myxzm123 来源:最后的格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