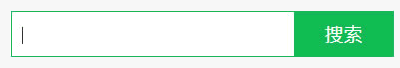照旧依着礼,拜了堂。
新郎行走时袍摆的药香冷清清散过来,我在旁不禁一阵恍惚。
高出一头的身量在黄昏辉光耀映下,斜打一溜清影,落在我绣花鞋尖。
这时的晏度还能行走。
顶着红盖头,我进了门,端坐床前,手指紧张拧着袖摆金线。
喜婆子在旁立定,正要说吉祥话,晏度伸手制止。
「不了,都下去吧。」
他的声音低沉动听,像冰落瓷盏,或落雪有声。
虽瞧不清样子,我却惊觉自己并未忘记他的样貌。
那双暗湖似的眼睛,望着人时,一点一点的光都被吸进去。
掀开盖头,我愣愣与他对视。
他的眼里,平静深处含着些许对猫儿狗儿般的怜悯。
「冷着了?」
我回过神,指尖微微颤抖。
是了,我真真确确地活过来了。
冷?自然是冷的。
寒春的河水结着薄冰,坠下去时,还能听到耳边「咔嚓」的碎裂声。
这些事,这种恐惧,我如何能与他交代?
只是顺着话,怯怯点了点头。
晏度垂眸看了我一眼,说:「冷就上床窝着,我这里,没那些规矩。」
说完,他就抬步去了屏风后的书案。
不一会就有几个侍女送来暖炉、汤婆子,再噤声离开。
屋子里静得只闻呼吸声。
我梳洗完,倚在床边看晏度投在屏风上的影子。
一时想不通。
他向来都是不喜情爱纠缠的人,就连财产经营也是受先祖父遗命才接手。
若不是那一纸遗书撑着,他连药都懒怠喝。
七情六欲出了世,死了都不会带去一丝牵挂。
这样的人,怎么可能会在临终前嘱咐不准我改嫁,拖着我给他守寡。
必是那俩中山狼兄弟出的主意。
我心里恨极,暗暗发誓定要他们不得好死。
这时,晏度处理完府务,散下头发,静静立在我面前。
我忖度片刻,默默抬脚往床里挪。
灭了烛,两人平躺而睡,过了许久,才听晏度轻声问:
「你唤薛妩,可有小字?」
黑暗里,我睁着一双清明的眼睛,抿了抿唇,忽然小心侧过头,依偎在他肩旁。
他身体僵了僵,终究没有躲开。
「缘缘,缘分的缘。」
语气柔和,仿佛无骨无依的藤蔓,嗅着他衣间的药香,汲取他本不暖和的温度。
我知道,他的病远没有到无药可医的地步,只是这人自己不想活,大罗神仙也救不了。
可是……凭什么娶了我,又不好好护着我。
我慢慢抬手摸上他的鬓角,像条阴冷的小蛇,柔弱犹豫讲着软话:
「官人……我怕得很,府里这样大,我一个人也不认识,只有你……」
他微微侧眸,细长手指迟疑抬起来。
两只同样冰凉的手,握在一起,仿佛一场化不开的春寒。
「我不是可托付的人。」他这样说。
我的心沉了沉。
却见他放开手,一双眼淡淡注视,「但,有我在一日,便无人敢欺负你。」
有这句话,就够了。
我柔柔一笑,睡回原位,嘴里还讨好道:「官人真好,缘缘此生都有依靠了。」
他低眸看着我拉开的距离,没有说话。
编辑:iihuo68 来源:步步灼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