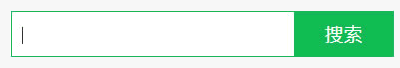上次见面,还是元旦,新年假期。
谢鹤逸去外地出差耽搁了行程,回来时孟臾已经歇下了。
黑洞洞的深夜,他敲开她的门,将她从梦中弄醒。孟臾吓了一跳,不由得睁大眼睛看他,却被他用手握住腕子压在床上,沉声命令道:“闭眼。”
她条件反射似的照做,刚听到床头灯被打开的“啪嗒”声,随即便被海浪卷走。
他的一双手仿佛有魔力,所过之处野火遍地。
孟臾觉得自己像是一团蒲草,立时三刻被他擦着点燃,随即投身入欲海。但这火是天火,水扑不灭,于是她只能在波涛间沉浮。
他吻她的锁骨,胸脯,腹部,甚至……花心。
温柔精巧的,从上到下,令她燃起来,却不至于烧干。
欲潮巅峰,随着他的猛然进入,三分疼痛带着十分畅快一齐袭来,她低吟出声,不住含糊叫他,“哥哥……”
最后,孟臾累得手指都不想抬,阖目仰卧在床边,长发披垂在地板,谢鹤逸躺在她身侧,一手横过她细瘦腰肢,就这样抱着她囫囵睡到天亮。
以往,他们是从不同榻而眠的,除了刚来谢园那几年。
孟臾的屋子就在谢鹤逸小楼的正后方,刚开始住过去时她年纪小,不习惯一个人睡这一整座屋子,总是整夜整夜地做噩梦。
一夜都是父亲的病入膏肓,母亲的决绝出逃,她站在漫无边际的极端黑暗中,不断从千仞悬崖跌进万丈深渊,梦里坠落前的那一刻,总有人伸手拉住她,惊醒后,她能清晰回想起,那是谢鹤逸的脸。
孟臾经常哭醒后,大半夜抱着枕头满脸泪痕去找谢鹤逸,他很少说话,但总是像抱猫似的不停用手掌轻抚她蜷缩着隆起的脊背,有节奏地拍哄她入睡。未成年之前,她为数不多的安全感,都是从谢鹤逸那里得到的。
车子驶入谢园,最终停在一座二层小楼前。
谢鹤逸没等裴渊,兀自推开车门下去。
孟臾低垂眼睫,跟上楼去。
这一晚,谢鹤逸做得很不克制,这简直不像是他。
孟臾就像在坐过山车,在他身下辗转着反复被推到最高处。
他紧紧拥住她,把头埋在她纤瘦的肩颈间,不断吮吻她耳后那一寸肌肤,流连不去。那一方小小的地方被他吻得微微泛红,孟臾甚至觉得有一点蛰痛,但这点儿微不足道的皮肉之苦不算什么,随之而来的是身体更深层次的愉悦。
她所有情事经验都来自于谢鹤逸,只要他想,轻而易举便能让她缴械投降。
他的指腹摩挲擦拂着她胸前的皮肤,不重不轻,却足以调动她的欲潮,一波强过一波的快感让孟臾几近失神。她扬起纤细脖颈,放任自己沉沦在欲望与痛楚交织的深井中,不断急遽上升再迅速旋落。
不知怎的,孟臾突然想到,外界说的谢鹤逸信佛,不执,不妄,不近女色。
那她到底算什么呢?
察觉到她的走神,谢鹤逸惩罚似的向前挺动了几下,伏在她耳边哑声问:“想什么呢?”
孟臾摇摇头,咬住下唇,抬手攀上他的肩,微微颤抖着***出声。
和往常无数次一样,孟臾依然没有在谢鹤逸身边留宿,结束后,趁着他去浴室,回到后院自己的屋子休息。
隆冬清晨,灰白天光照进雕花门扇。
李嫂推门走进厅里来,隔着屏风在外面叫她:“孟小姐,先生快起了。”
她是谢家积年的老人了,嘴里的先生指的自然就是谢鹤逸。
昨晚孟臾睡得不好,她倒在枕上,闭着眼睛皱眉用力吸了几口气,抬手捂住额头试图缓解昏沉欲裂的头痛,扬声答:“知道了,收拾好就过去。”
但她这大半年在学校宿舍懒散惯了,没立刻动,又加一句:“他昨天喝酒了,来得及。”
见里面没动静,李嫂也没动。
她并不催促,只是不离开,不急不缓站在原地等,隔了不到两分钟,孟臾再赖不下去床,挺身起来,去里面浴室洗漱收拾。
这就是谢园的规矩,就算叫人一巴掌扇了个晕头转向,谢鹤逸的事儿也是一秒钟不能耽搁。你不想懂规矩,有得是人教你。
孟臾换了衣服出来,站在屋前廊檐下拢着蓬松长发,伸臂踢腿舒展几下筋骨。
雪已经停了,但天色依旧阴沉,仿若低压震地,让人心头憋着一口气。
放眼眺去,孟臾看到前院二层的楼檐和檐下的半扇窗子。雀鸟落在檐上不断啾鸣,一身灰扑扑的羽毛,蹦蹦跳跳地,活泼得厉害。
谢鹤逸让李嫂安排人每天在固定地方撒上米粮,久而久之,雀鸟习惯被人饲喂,这枯山瘦水的园子里便又多了一景。
雀鸟为稻粱谋是物种本能,人又何尝不是?
孟臾不再看,抬脚往前院花厅走去。
花厅里没人,孟臾攀着楼梯扶手上了楼。
谢鹤逸的祖母谢晚虞出身江南的大地主家庭,那个时代真正的书香门第娇养出来的世家大小姐,投身革命嫁给了谢鹤逸的祖父。谢鹤逸自幼便跟着她长大,养成非常自律的起居习惯,不管前天晚上多晚才睡,次日都不会晚于七点起床,所以李嫂才会一早就去叫孟臾。
不像话。
没见过哪家的近侍起得比主人还晚的。
是的,谢晚虞活着时,整座谢园在她的示下中默认的孟臾的尴尬身份,大概相当于封建社会的通房丫头?
浴室的门半阖着,洗漱的动静从门缝里泄出来。
孟臾没进去,也没敲门,安静地抱着胳膊靠在门口等,透过旁侧的雕花窗向外看去。
直到离开去住大学宿舍的这几年,她才像是终于体会出这宅子一点半分的好处,开阔的园子,苍翠的青松,枯败的银杏,雪色压在灰瓦屋檐间,似乎找到了皈依。
谢鹤逸收拾好拉开门,散落的额发还带着潮湿的水汽,眉眼霁明的样子。见到门口的孟臾,他先是一怔,接着揶揄:“一大早站在这里给我当门神呐?”
“等你一起吃早饭。”孟臾鼻尖微动,谢鹤逸身上有股清冽冷淡的薄荷香气,不知道是牙膏还是须后水的味道。
谢鹤逸蓦然凑近她,手指虎口卡在她的腰侧托着她的腰臀踮起脚尖,呵笑一声,“离近点闻。”
头顶上有片阴影覆下来,孟臾被这突如其来的压迫感笼罩住,仰头看着他呆呆问:“你换须后水的牌子了?”
谢鹤逸失笑,眉梢扬起来,双手揽住她的腰背,额头低下来向她颈间靠近,迅速拉近了两人之间本就不太宽裕的距离。
“喜欢这个味道,嗯?”他伏在她耳边问。
谢鹤逸口鼻腔的震动喷薄而出的热气,就这样从孟臾的耳廓顺着颈椎一路向下到达脊背,她的身体蓦地酥麻了一瞬,脸颊也开始微微发烫。
孟臾心下懊恼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。
多可怕,这具躯体仿佛是被他随意操控的傀儡,轻易就对他起了难以抑制的热烈反应。
白天的时候,孟臾总是自欺欺人地不太愿意亲近谢鹤逸,她觉得自己有一种奇怪的羞耻心,哪怕谢园上下所有人对他们的关系都早已心照不宣。
孟臾出于本能地折着身子向后撤,一边用力推他箍着自己的胳膊,嘴硬道:“有点苦,我喜欢原来的。”
谢鹤逸哪里肯放过她,将她抵在墙上,捧着她软嫩的脸颊蹭上玲珑的鼻尖,“狗鼻子。”
然后便俯身吻起来,孟臾被他亲得渐渐有些喘不过气,毫无缝隙地无限贴近让她面颊滚烫,整个人像是躺在温软缱绻的云朵中,膝盖酸软地几乎站不住。
“不要了……”孟臾紧促地呼吸着,试图平复波涛汹涌的欲望,她双手揽住谢鹤逸的脖颈哼唧着求饶,脑袋趴在他的肩窝里,“我饿了,先吃饭吧。”
花厅里几上已经放了几碟小菜,两碗白粥。
菜品简单,色泽也偏淡,看着就素净。
谢鹤逸口味清淡,而且吃的不多,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什么口腹之欲,敷衍地厉害。
所以他的餐食一向好对付,谢园的厨子应当是宅子里最轻省的差事儿,只要没有大差错,从来不会惹恼他。
但是今天,谢鹤逸显然心情不错,慢条斯理地吃了一碗粥。
孟臾原本就没什么胃口,期间桌面上手机震动,她顺手划开屏幕,见是朱惊羽发来的消息,问她昨天见到的那位“贵客”的事情。她怕说漏嘴给谢鹤逸造成什么麻烦,索性彻底放下碗筷全神贯注的应对。
朱惊羽连续发了好几条微信消息:
「李经理托我再好好跟你说说,请你年后再来,报酬翻倍」「师妹啊,这种时薪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哦」
「当然啦决定权还是在你」
孟臾回:
「谢谢师姐」
「我就不去了」
「年后要忙毕业的事」
隔了片刻,朱惊羽又发了两条:
「我跟你说实话吧,李楚明说苏六爷跟那位贵客的生意还没谈完,要我尽力说服你,哪怕只是在贵客来的时候过来弹也行啊」「你再考虑一下」
孟臾蹙眉,轻叹口气,为难地啧了声。
谢鹤逸吃饭时很少说话,所以一直静默地看着孟臾脸色变换。
谢晚虞在世时,他们三人经常一起用饭,孟臾根本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在席间看手机,但她在谢鹤逸面前就敢,敢挑食,敢做一些不太符合她性格的事情。
“不是说饿了?”谢鹤逸推开碗碟,拿起手边的餐巾沾沾唇角,“什么事为难成这样?”
孟臾放下手机,没有隐瞒地坦诚道:“我在如是观弹琵琶的兼职是一个师姐介绍的,她受人之托,想让我年后接着去……”
她抬眸觑了眼谢鹤逸的表情,连忙转了话锋,“我正拒绝呢。”
谢鹤逸随意道:“我跟苏六说一声。”
“不要不要,你出面,我就更说不清了。”孟臾脱口而出连声拒绝。
说不清什么?无非是他们到底什么关系,他又为何要为了这种小事兴师动众。
她强调:“我自己能解决。”
确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,所以谢鹤逸并不坚持,没再多说什么。
苏六之所以不遗余力讨好他,无非是想从他手里握着的众多项目中分一杯羹,但与这种灰色地带起家的二道贩子合作,风险到底摆在这儿。这半年来,苏六中间七拐八拐地托了好几重关系才把请柬递过来,他不得不斡旋一下,没想到可巧就在饭局上遇到了孟臾。
孟臾想起来什么来,调笑道:“说起来,苏六爷这人也挺有意思的,哪有请人吃饭点《十面埋伏》的。”
谢鹤逸促狭问:“哦?那你怎么不提醒他?”
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咯,况且,万一贵客就好这口呢,哎——”孟臾惊呼,话音刚落,她就被谢鹤逸托着腰用力拽到近前,她一个趔趄,跌入他清冷的怀抱之中。
他抱着她调整姿势,让她岔开腿跨坐在他大腿上。
谢鹤逸轻轻笑了声,“嗯,你说得对,贵客就好这口。”
编辑:iihuo68 来源:囚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