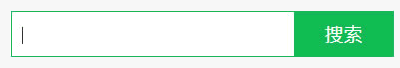车停在庄园内,周惟深拎下花篮,大步走进高於十几层的豪宅。
佣人们正紧锣密鼓布置着明日的宴会场。大寿过九不过十。海云马上要奔八十了,这是件喜事,散在全球各地的这一支周家人都要回来给老太太庆寿。
不过老太太忌讳旁人说她年纪大,无论什么身份,一概称她“海云”。
见着周惟深回来,佣人们高兴起来,纷纷喊着:“大少爷!”
“海云呢?”他问。
“海云在楼上和婉秀太太还有明嘉小姐在打牌。”
“我母亲呢?”他问。
佣人有些支吾。你瞧瞧我,我瞧瞧你,没人敢说。
周惟深脸色微沉,“有话直说。”
“海云想给大太太认个义女,大太太不同意,午饭时候俩人争了几句,大太太没吃完饭就放了筷子回房间,现在还没出来。”
不待他再问,佣人自觉补充道:“先生一早去了酒庄,说要晚上回来。”
周惟深拎着花篮上了楼,总管跟上他脚步,继续说家里情况:“二少爷还没回来,明嘉小姐一直陪着海云在打牌,庄怡小姐同姐妹出去打高尔夫了。二先生明天上午到老宅,冬婵姑姑改了航班,明天下午到老宅。”
周家人丁兴旺,有海云这个“老顽童”带头,家里称谓也乱得很。除了老派一些的长辈按主次叫,家里小辈的姑娘都是叫名字和称谓,不分大小。周冬婵是他姑姑,小时候家里人跟着他喊着喊着都叫起了姑姑。
他一到家当然得先去见长辈。
海云在棋牌室。周惟深还没进门就听到她在中气十足地喊:“大玖!”
海云背对着大门,周眀嘉和秦婉秀都看见了他,面露惊喜。他比了个噤声,走到海云身后,伸手蒙住了她的眼睛。
海云的牌掉了,她“呀呀呀”三声,“晏川,你还晓得回家呀?”
大家一下哄然笑了。
“海云,你回头看看是谁。”秦婉秀忍俊不禁。
周明嘉起身,做了下口型,无声喊道:“大哥。”
周惟深看向她,微微颔首,食指和中指并拢,朝下一弯,示意她坐下。
海云回头一看,发现居然是她那个大半年没见过了的大孙子。
她一下牌也不打了,拉着周惟深的手道:“不是说晚上回来吗?怎么下午就到了?”
“海云,我说的是国外时间,不是中国时间。”
“我哪知道你说的时间还有时差啊?早知道你这个点回来,我让厨房晚点做午饭的。你吃了没有?”
“吃过了。这是给你的花,你看看,喜不喜欢?”
海云这才注意到他还拎了花篮,她一见心喜,嘴上还说着:“哎呀,怎么想起来送花了?”
“喜欢吗?”周惟深将花篮放在了牌桌上。
花色明艳而不轻佻,大丽花庄重,望鹤兰高雅,层次立体得当,一看便觉富丽雍容。
秦婉秀道:“这花是费了心思的。”
“得当得当,待会放我房里去。”海云拍着周惟深的手背。
他微微俯身,凑在海云耳边道:“是母亲叫我送你的。”
“我就知道你没这心,”海云锤了他一拳,不满道,“拿走拿走!”
“拿哪去?”
“当然是我房里!”
大家便又都笑了。
“你们继续吧,我去看看母亲。”他向众人颔首示意。没在海云面前问义女是怎么回事,这事听一个人说就够了。
他去见母亲是礼数,没人拦他。
周惟深拎着花篮走出去,递给总管,“放海云房里去。”
母亲房间在七楼,房门紧闭着。
他叩了叩门,道:“母亲,我回来了。”
没人应。他自顾自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卧室分三进,第一进是休息区,第二进是睡房,第三进是衣帽间和洗手间。
房间里春妈妈在陪着母亲。
春妈妈一扭头,看见他站在睡房门口,吓一跳,随即又欢喜起来。
“太太,惟深回来了!”
木苒芬撑着床坐了起来,垂泪道:“惟深!”
“这是怎么了?我回来了母亲不该要高兴吗?”他笑着,故意不解。
木苒芬趴进了他怀里,哭诉着:“我要被人欺负死了!”
他坐在床边扶住她,好笑道:“谁欺负你了?”
春妈妈帮嘴:“海云不问太太同意就要给太太收一个义女,太太年纪大了,哪还受得了这折腾呀!”
周惟深这才敛了笑容,正色问:“什么义女?”
“是酒厂顾家的女儿,上回酒会,海云瞧见了顾家二女儿,觉得像……”春妈妈吞吞吐吐。
周惟深追问:“像什么?”
“像周秋荷。”
提起这个名字,周惟深也微怔。
周秋荷是他已故的大姑姑,十多年前生产羊水栓塞走的。
打那之后,这个名字就成了家里的一块隐痛。
周明嘉就是秋荷姑姑的遗孤。
海云把孩子从姑父家要了来,随了周家的姓,上周家的族谱,聊寄哀思。
只是周明嘉长得像姑父,浓眉大眼,生得有几分英气,不像秋荷姑姑一双凤眼,清丽温婉。
他问:“酒厂顾家哪个姑娘?”
“二姑娘,顾以宁。”
“母亲不喜欢她?”周惟深问。
木苒芬推他,“平白无故给你多个妹妹,你愿意?”
周惟深笑,“我又不常在家,有人能在家陪母亲,我当然高兴。母亲是有别的缘故吧?”
“我和周秋荷自幼不和,现在她走了,那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也就不提了,可是你知道海云怎么说我吗?”
他耐着性子问:“海云说什么?”
提到这,木苒芬又悲从中来,“她说我只有两个儿子,没有女儿,只能凑个孤字,以后是要孤独终老的!”
孤?
周惟深久在国外,不常写汉字,想了下偏旁部首,问:“那我和周晏川,谁是瓜?”
编辑:iihuo68 来源:缦塔与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