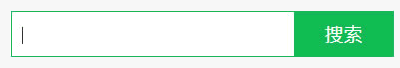7.
我们从矮墙上翻进后院,按理说那一院子的狗看见生人应该狂吠才是,它们却动也不动地趴在地上。
阿芮蹲下去查看。
“它们好像是被下了药。”
我看了一圈,院子里拴着的这些都是成年健壮的大狗,它们可能就是即将被卖出去的那一批,给它们下药应该是怕它们反抗。
而白天被拉出去表演的那些狗并不在这里。
“姐姐,怎么办?”
“再看看。”
后院的西南角还有一栋小楼,我们顺着楼梯上了二楼,有三个房间,都关着狗。
听见动静,它们立刻开始大叫起来。
前院走出来一个人,拎着棍子,恶狠狠地大骂道:“妈的,你们这些畜牲,再叫老子把你们宰了!”
那些狗果然不敢再叫。
我们放轻脚步小心翼翼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看过去。
第一个里面关着白天被拉出去表演的狗,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最多,小的大的老的都有,大多都被打得遍体鳞伤,缩在角落里轻舔伤口,而第三个房间则关着很多怀了崽的狗妈妈。
看到这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狗场老板是在做什么生意,学得会技能的狗就拉出去卖艺,学不会的就打,打了还是学不会的就养着卖给馆子里,母狗则留下来继续繁殖。
阿芮气得握紧了拳头。
“我要给那个糟老头下最毒的药!我要让他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!”
我正欲说什么,看到矮墙那又翻进来一个人,我赶紧拉着阿芮躲起来。
来人穿着炫目的红衣,背着刀,身手利落,只见他惟妙惟肖地学了两声狗叫。
之前那个提着棍子的男人又气势汹汹地走过来,被他一个手刀劈晕。
他利索地解下一根狗链,把男人绑起来。
此时又进来一个人,刚好看见红衣男子在绑人。
他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棍子,大声问:“什么人?”
红衣男子转身,抽出背上的刀,三两下就架在他脖子上。
“我是你爷爷。”
他很快也被绑起来,红衣男子把刀扛在肩膀上,一只脚踩着一旁的笼子,问他:
“你们的狗哪来的?”
他眼神闪躲,“捡的。”
红衣男子用刀指着他:“再回答一次。”
“大......大部分是偷的。”
“都关在哪里?”
“除了院子里的,其他都在小楼上。”他指了指西南角的小楼。
“钥匙给我。”红衣男子伸出手。
“你们俩干嘛呢?动作快点,赶紧装车把狗送过去!”老板骂骂咧咧地走进后院。
我扔出一个飞镖,打飞了他的帽子,趁这个间隙,红衣男子翻身到他面前。
明晃晃的刀当即就吓得他两腿瘫软,“好汉饶命!”
“把这些狗放了,从哪偷来的送回到哪里去,我饶你不死。”
老板转了转眼珠子,“好汉吩咐的我照做就是!”
“别信他,他想跑!”
“珍珠,拦住他!”
阿芮跑下去,那个老板想趁红衣男子放松警惕的时候跑出去,幸好她让珍珠堵住了门口。
看见大蛇,老板直接被吓晕了过去。
红衣男子又解下一条狗链,把老板也绑了起来。
“多谢你们出手,不然真叫这老杂碎跑了!”
红衣男子朝我们拱拳道谢。
“不客气,我们目的是一样的,自然应当帮你。”阿芮摆摆手。
“可是这里这么多狗,该怎么处理?”
原本姐姐是想把表演的那些狗狗买回去,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狗。
“它们大多都是家养的狗,只是被偷出来这么长时间,恐怕很难找到它们的主人了。”
“能找到主人的就送回去,找不到的就找个地方养着吧。”我说。
这些年我存了不少钱,给它们一个家,不成问题。
“那他们三个呢?”我指指地上的三人。
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确实令人愤怒,但当朝律令并没有哪一条规定了不能倒卖动物,他们最多是犯了偷窃罪,即使送去官府也不会被严惩的。
若放在以前,也许我真的会砍了他们,但现在,我不想杀人。
“送他们去伶馆,不是喜欢卖艺么,也让他们尝尝其中滋味。”阿芮说。
我毫不怀疑这是她能想到的最不残忍的手段了,如果不是我拦着,这三人可能已经染上了不止一种毒药。
一阵微风吹来,丝丝凉意侵入我的肺腑,我抑制不住咳嗽起来。
阿芮赶紧扶住我,对着红衣男子说:“就这么说定了,你去办,事成之后来轻风小筑找我们。”
她扯下老板身上的荷包丢给红衣男子。
8.
红衣男子来找我们是在三日之后。
他告诉我们他之前借住在一个大娘家,他们家有一条黄色的大狗,但有一天夜里离奇失踪了,后来村子里又有很多狗都失踪了,他就一路追查,直到在洛水镇看到这个让狗卖艺的队伍,才决定跟着他们一探究竟。
没想到还真是他们干的!
这三天他连夜赶路,把那三人送去另一个城市的伶馆了。
我告诉他给狗安身的院子也找好了。
准确来说,是林止找好的。
那天从狗场回去之后,我们跟他说了当天发生的事,他也同意找个院子给那些狗安家。
没想到第二天房契就送过来了,不仅是房子,林止还找好了照顾狗的人。
他们原本是流落街头的乞丐,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有个安身之所。
只要把狗照顾好,他们还有月钱能自己开销,他们对林止感恩戴德,林止却不甚在意。
我说我也出一份力,狗和人的每日开销也算一份在我头上。
他说他存在钱庄的银子已经足够了,他们会每月给狗舍送钱的。
我发现他真的很有钱。
吃穿用度皆为讲究,遇见他的这一路,我的生活都跟着上了一个档次。
我有一种白嫖的罪恶感,我说:“林止,我给你打工吧,不用给工钱。”
林止说:“你救过我的命,我养着你理所应当。”
可是他大概忘了,他也救过我,还不止一次。
我又问:“那阿芮呢?”
“她要用药养你,我养着她也应该。”
“那方不苟呢?”
“他不行,他得给我打工。”
我笑笑,林止还真是......有一种莫名的可爱。
方不苟就是那个红衣男子,他来了轻风小筑之后,被阿芮的厨艺俘获了,每日不来蹭上一顿饭就不甘心。
后来林止干脆让他给我们当护卫,没有工钱,但是包吃住。
方不苟本来是有些纠结的,他这一趟是出来游历江湖的,让他困在一个小院给人当护卫,这着实和他的想法背道而驰了。
但后来听我说我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呆太久,之后也会四处走的时候,他马上同意了。
多一分犹豫都是对阿芮的不尊重。
给方不苟办欢迎宴的那晚上,也许是酒意上头,也许是气氛到了,那是我们四个人第一次交心。
方不苟的家庭并不是达官显贵,但衣食无忧,生活还算富足。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,从小便是父母的掌中宝,他想学武功,父母就送他上山拜师学艺,他想闯荡江湖,父母就给他准备盘缠吃食,他的一切决定他的父母都很支持。
他们最大的期望,就是他能光明磊落做人,不行不苟之事。
阿芮说她是从西域来的,那是一片对我们来说神秘莫测的地方,虽是王朝国土,却不曾见人来中都参拜,听闻那里毒物众多,外人去了九死一生。
她说她是从家里逃婚出来的,在西域待了十七年,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,她不愿意就这样嫁人一辈子被困在那里。
林止告诉我,他和阿芮差不多,都是家里想让他做他不想做的事,所以他跑了出来,仗着武艺傍身,一路从南境到北疆,从北疆到东海,游历山水,游戏人间。
遇见我的时候,他正准备从东海出发,一路向西,说不准能看看传说中的西域到底是何模样。
编辑:iihuo68 来源:最后的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