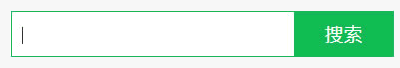那三年,我和朱栩正蜗居在国外那间潮湿阴暗公寓里。
他一为治疗,二为隐姓埋名避祸,与家族断了联系,生活非常窘迫。
我每天打几份工忙到半夜,还要照料他身体。
累到站着也能睡着。
做康复时,他一米八的个子压在我瘦削的肩上,我硬生生地扛住,逼着他一步步地走。
他崩溃发疯,狠狠摔打盘碗,砸在我额角上,血流到我晕眩。
也不是没有过温暖的时候。
冬夜里公寓冷到滴水成冰,我们互相依偎取暖。
他毛茸茸的头发挨着我的鼻头,像只小狗。
他也曾喃喃说过,既然许家要我替嫁,那我未来便是他的妻子。
也许患难之时,说过的话大多都是一时感触胡言乱语,当不得真。
回国后,我被朱栩正圈养在市郊一个小别墅里。
他以我母亲的医药费要挟,不许我离开西京半步。
他也未曾来看过我,只从乡下找回打小照顾我的刘阿姨,陪我同住。
刘阿姨常念叨,我这三年陪着朱栩正吃尽苦头,总算等到他身体痊愈,收回家族大权,他必定是会念及我的好。
只是我脾气太倔,不肯服软,才惹得他生气。
连生了这么大的病,也不让他晓得。
西京的冬天冷得很,我整夜整夜咳嗽不止。
除了刘阿姨,没人知道,我的第一轮化疗已经过半。
编辑:iihuo68 来源:朱重山许青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