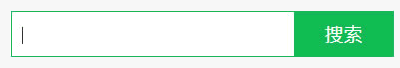驰经,乃我的大师兄。严格来讲,是这些年与我被传作天作之合的大师兄。我拜入师门之时,年岁尚小,自小到大,驰经对我最为照顾。大师兄温文尔雅,曾经是我在宗门内最为信赖之人。然而,这最为信赖之人,却在当年那场残杀我的盛宴中,目光狂热,连眉头都未皱一下。——只因事后,他分到了其中最好的一块仙骨。后来符无归杀上青山宗,首个被杀之人,便是他。
这辈子,我不愿符无归再增添更多杀孽了。这笔债,我要亲自讨回来。玉牌闪烁,符无归显然注意到了,他停下动作,双指捏住玉牌,似笑非笑道:“不听听看?说不准,是有什么急事。”话语说得轻松,他捏着玉牌的手却青筋暴起,仿若恨不能将其捏碎。我眼皮直跳,迅速伸手切断了传讯。可下一刻,玉牌又亮了起来。他擦拭了一下唇角,后退一步,颇有风度地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他站在一旁的模样,实在算不上温和有礼。……反倒像猛兽在发动最后攻击前,象征性地压低身子。我硬着头皮打开传讯,驰经的声音即刻响起,满是担忧:“鸢儿,你真的去杀那个魔头了?虽说他有伤在身,但依旧不可小觑,万不可硬来!你我婚约刚定,就当是为了我,也要保护好自己……”察觉到符无归周身的威压骤然加剧,我手一抖,在驰经将话说完前,失手捏碎了玉牌。
而后不合时宜地想起“欲盖弥彰”这四个字。“符无归你听我解释……”我顿了顿,重生一事太过诡异,我尚未查清其中奥秘,还不是全盘托出的时候。就这一顿之间,他垂下视线,以难以看清的速度出手,掐住我脖颈,压在墙上。他的五指指尖化作利爪,我曾亲眼目睹这只手如何将大荒中最为凶猛的凶兽开膛破肚。只因那只凶兽舔舐了一下我的尸首。空气愈发稀薄。
我直视着他的双眼,清楚知晓他不会真对我下手。——就如当下,他尖利的指甲按在我颈间脉搏之上,却连一丝血痕都未留下。虽然我自己心里清楚,但神兵利器皆有护主之能,早先被我扔下的破渊剑感应到我的危险,颤颤巍巍飞了起来,剑尖对准符无归的后心。他仿若未觉,任剑尖刺破衣裳。倘若忽略他过于浓稠的视线,当下这情景,堪称一句不死不休。
符无归不松手,破渊剑急了,眼看着就要刺破血肉——我伸手环住他腰身,借了巧劲,将他压在身下,调换了位置。破渊剑茫然停滞,无精打采地掉落在地。其实那一剑刺下去也无妨——他的真身乃是龙,龙是有护心鳞的,死不了。他也的确会放任我一剑从他身后刺入。直至上辈子目睹他孤身屠尽青山宗,我才醒悟,符无归从前与我的那些,皆是小打小闹。
他从未尽过全力,仅是纵容着我在其身上留下一道道伤痕。我紧紧抱住他的腰,趁他下意识松手的间隙,迅速说道:“符无归,喜欢你是实打实的,并未骗过你。婚约并非我的本意,往后我会向你解释清楚。你信我这一回,行不行?”掐在我颈间的手放松了力道,利爪消散。
但他仍旧以指腹反复摩挲我颈间脉搏,似乎在掂量我的话是否可信。我忍不住补充了一句:“真的!”符无归低声笑了笑,喉结滑动,“证明给我瞧瞧。”方才几番拉扯之下,他的衣带早已松开,衣襟敞开,袍子松垮地挂在身上,显露出分明的线条。我勾住他的脖子,将他拉低一些,不由分说地吻了上去。我也忘却了我们是如何滚作一团的了。只记得起初貌似是我更为主动,符无归还有些惊愕,大概从未料到我会对他如此。
后来不知何时起,跃跃欲试的雀鸟被觊觎已久的恶龙纳入爪中,无处可逃。一切结束时,天色已然大亮。传音玉牌碎了,大师兄的传讯也被打断,我若再不返回宗门,恐怕会无端生出变故。我摸了摸自己滚烫的脸颊,推开那只不知满足的手,坐起身开始穿衣。符无归自后面贴上来,在我肩窝蹭了蹭。刚刚他又是咬又是舔的,令人怀疑他的真身应当是某种犬类才对。
他突然含住我的耳垂,话语带着哑意:“招惹完了,就想走?”我猛地一颤,往旁边躲了躲,却恰好钻进他的怀里。“我还有些事得回去处理好。”他皱了下眉,“什么事?”大有只要我说出来,他就会逐一替我解决的态势。我在心中为魔域默默叹息。显然,他们这位魔尊,颇具昏君的潜质。“唯有我才能做成的事。”察觉到他有些不悦,我转身凑过去结结实实地在他唇上亲了一口,而后举手起誓:“最多十日,十日后,我必定去找你。”符无归的神情稍稍松动,抬手抓住我起誓的手掌,反复揉捏。
“十日后我若未见你,就算是掀翻青山宗,也定会将你揪出来。”啧,比我预想的要好哄太多。宗门内平静如昔。即便我一身新伤惹眼,从山门走回来的一路上,也无人问询半句。或许他们已然习惯了——他们那天资卓越的小师妹,哪次不是带着伤归来?反正小师妹灵力深厚,这点伤根本死不了。
我整理了下血迹斑斑的衣衫,前去拜见师尊。他命我去杀符无归,现今人还活着,我总归得有个能交差的模样。这身伤不过看着唬人,毕竟我持着符无归的本命剑对自己下手时,他人就在旁边看着,眉头皱得极深:“非回不可?”我点头,拿剑比划了两下,对准肩胛,狠狠刺下去——刚划破点儿皮,手中剑便被他夺了去。他神色不佳,“我何时对你下过如此重的手?”……罢了。曾经与我斗得不死不休的时候他是半句不提。
编辑:iihuo68 来源:月下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