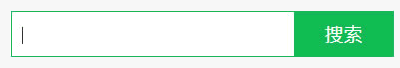此话一出,全场哗然,大家纷纷扭头往周志远和刘安安身上看去,讨论声越来越大,也越来越露骨。
围观的人都觉得今天真是值了,看了两场狗血大剧,这简直比之前公社放的电影还好看。
刘婶怔然地望向女儿,她从来没有一刻觉得女儿这么陌生过。女儿五岁时,丈夫就病死了,这些年她一个人辛辛苦苦拉扯大孩子,从来没有想过改嫁,担心嫁过去男人对女儿不好。
眼看着女儿养成了,也说了一个好婆家,再过几日就要订婚了,却没想到……刘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,她瘦弱的身躯晃了晃,似乎下一秒就要跌倒在地。刘安安大惊失色,赶紧扶着刘婶坐在旁边的碾子上,焦急地问道:
“娘,娘你怎么了?你不要吓我啊!”
刘婶深吸一口气,用力地挣脱女儿的搀扶,别过头不看她。
刘安安又惊又气,随后又恨又怒地扭头指着沈秋骂道:
“你不要血口喷人!我承认,我和周知青互有好感,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!因为心里明白大家各自将要组建家庭了,所以我们真诚的祝福彼此!
你自己立身不正和陆霆华睡了,就想要给我们扣屎盆子,我告诉你,做梦!”
陆霆华眉头皱了皱,眼前歇斯底里的女人与他印象中乖巧文静的女孩大相径庭。想到那碗端给自己的金银花茶,真相如何不言而喻。
他担心地望向沈秋,却没想到沈秋不怒反笑,
“如果你们之间清清白白,那你告诉我,你右边锁骨上的吻痕是哪里来的?你衣襟上的白色硬块,又是什么?最重要的是,既然你们真诚地祝福彼此,那你又为什么煞费苦心地给我和陆霆华下药?”
刘安安心下大乱,眼神慌乱地低下头,一只手用力捏住衣襟,另外一只手捂住锁骨的位置。
今天下午休息时,周志远说自己憋得不行了,所以她用手帮他纾解了一下,因为当时记挂着这边的事,没有仔细清理,没想到竟然……她不敢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目光,这会儿肠子都悔青了,要知道沈秋知道这么多事,她说什么也会找一个更稳妥的办法,也不至于现在弄得自己这么狼狈。
一张小脸煞白,鬓角冷汗涔涔,她只能强撑着反驳,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我一个农村人,哪里来的药?你说假话是要负责的!”
沈秋怜悯地看了眼精气神散了大半的刘婶,摇了摇头:
“既然你不到黄河心不死,那我就说得再明白些。
刘婶因为早年劳作力度太强患上了风湿,这些年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转。三年前你私下跑去隔壁县的向阳村,找了住在牛棚里的一个古怪老太婆,从她那里得了一个治疗风湿的方子。那个方子很管用,你为了感谢那位老太婆,每隔一段时间,就会托人给她捎些东西。
而非常巧合的是,就在我和周志远收到家信的第二天,你就说自己最近不舒服,吃药看不好,所以找大队长开了介绍信,我记得介绍信上写的,就是隔壁县吧。
你能告诉大家,你得了什么病,那位老太婆给你开了什么药吗?”
见刘安安还想找借口,沈秋不耐烦地打断她:
“刘安安,我今天既然敢把这些事情当着大家伙的面和你掰扯,肯定是掌握了证据才说的,所以我劝你,找借口的时候不要太离谱!”
刘安安咬紧下唇,期期艾艾地望向周志远,期望他能帮帮自己。却没想到周志远满脸失望地看着她,最终颓然地蹲在地上,双手用力揉搓着头发。
陆霆华眼神复杂地望向刘安安,他没有想到,平日里在自己面前腼腆乖巧的女孩,竟然有这么狠辣的一面。
刘安安见周志远不理她,心内惶惶,又扭头去看陆霆华,期冀他能看在从小长大的情分上为自己说句话,但陆霆华见她看过来,厌恶地拧眉看向一边。
村里人鄙夷地看向刘安安,嘴里的话像是刀子一样割在她的脸上、身上。
“这刘安安平日里看着柔柔弱弱的,和谁说话也笑嘻嘻的,没想到私下里竟然这么狠,为了抢男人,竟然给别人下药,咱们以后可离她远着些。”
“说到底,还是华子可怜,这么多年两家都默认要结亲家,华子可是没少帮着刘家上工赚工分,哪回不是先忙完刘家的活再去干自家的?没想到竟然养出一条白眼狼!”
“可不是吗,刘婶身体不好,昨天分给她的田,麦子只割了一小半,剩下的都是今天早晨天还没亮,华子去给割的。”
“人再好有什么用?你没听沈知青说的,人家周知青家里早早准备把孩子调回城去了,如果刘家丫头跟周知青结婚,就变成城里人了。再过两年给安排个工作,那跟咱们这些泥腿子可就天差地别喽。”
“照你这么说,这刘家丫头是想抢沈知青回城的名额?妈呀,这也太狠了,为了当城里人就设计坏人名声。”
“要不说最毒妇人心呢!”
“哎呀,等双抢完了,我得赶紧让人给我侄女捎话,她早早就相中华子了,只是因为华子和刘安安有婚约,所以一直没说。这么好个后生,我得给我家侄女看紧了!”
“他婶,你别瞎忙活了,你家侄女长得五大三粗的,和华子站一起,不知道的还以为兄弟俩呢。我娘家表妹长得特别水灵,手还巧,和华子一看就有夫妻相,我明儿就捎话回去,让两个人早早相看。”
“你这人咋做事不地道呢?我给你说……”
……
沈秋眼看着讨论的话题越来越歪,没忍住“噗嗤”笑出了声。
真没想到书中的男二号竟然是个香饽饽,这边婚还没退呢,那边就有人上赶着说媒了。
陆霆华也没想到这些婶子想一出是一出,听到沈秋的笑声,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,耳尖可疑地发红了。
不过还是正事要紧,沈秋扭头对头大如斗的大队长正色道:
“大队长,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,我说的你都可以找人去查证。您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?”
刘建设头痛地扶额,想他活了四十多年,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下作的阴私事。
刘婶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沈秋面前,二话不说跪了下来。沈秋连忙往旁边让了让,“刘婶,你这是做什么?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。”
周围平日与刘婶交好的婶子们也上前劝道:
“是啊她婶,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,你跪着,孩子们心里也不好受。”
刘婶摇摇头,常年劳作的脸上满是疲态,她眼眶微红,但神情坚定,“沈知青,安安和周知青的事,还有今天的事,是我们刘家对不起你,我该给你赔不是。是我没有教好她,才让她做出这种事。
我知道,她这次错的太离谱,就算你要把她送去蹲号子,或者是拉出去批斗,都是应该的,也是她应得的。”
她神情涩然,语气微哽,缓了缓后,才继续说道:
“我也知道我没脸求你原谅,但是她再不是人,也是我闺女,我是她娘,其他人都能不管她,我不能不管她。
今天婶子豁出自己这张老脸求求你,放她一码。安安还年轻,如果蹲了号子,或者被拉去批斗改造,以后,她这辈子就毁了啊……”
说罢,便瘫坐在地上崩溃恸哭,“安安你个死妮子,华子对你这么好,你的良心叫狗吃了?竟然还做下这种事,我,我以后死了怎么对你爹交代啊,呜呜呜……”
编辑:iihuo68 来源:穿越七零:糙汉独宠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