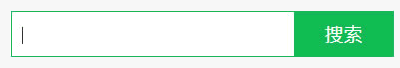离开原来的公司,平时随叫随到的我,开始选择性接听倪恩施的电话。我并不是在摆谱,只是我遇到了新的麻烦。
新部门的经理是个高高壮壮的中年男人,表面对我很是客气,讲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。可我知道,他并不欢迎我。
在接待客户的晚宴上,他将一整瓶白酒摆在我的面前,还是那副笑面虎的语气,他说,“陆经理来得真是时候,我最近体检查出一堆毛病,老婆给我下了死命令,敢喝一口酒就离婚。但咱这老规矩不能破,所以今天,就请陆经理代为主持一下。”
说完就真的坐下来,皮笑肉不笑地望着我。我只好站起身,望着围坐在桌边的一群中年男性,说是客户,其实都是他的老搭档。
趁着提前喝下的酸奶还贴在胃壁上,我端起面前的白酒,微微点头笑着说,“初来乍到,不敢逾矩。酒我先干了,权当热场。”
半斤白酒灌进食道,我感觉整个内脏都烧麻了。“确实不胜酒力,只能担个热场,接下来,还是得请王经理主持大局。”
我双手示意,将酒局还给王川。趁着三旬过后的空挡,我偷偷溜出包厢,躲进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,用手指抠出胃里的酒。喝酸奶、吃生鸡蛋、压舌吐酒,这些都是我在倪恩施那里学来的。这么多年,我跟着他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饭局中,他从不怂恿我喝一口酒。每回搀扶着烂醉如泥的他回到酒店,望着他发白的脸和垂进胸膛的头颅,有那么一刻,我的心头也涌过一丝酸涩。
尽管我知道,我们之间互不相欠,只是一场交易。
吃饱喝足之后,男人们的乐趣便是去做足疗按摩。我借口身体不舒服,躲在隔壁包厢等着结账。中途手机没电,我出来租了一次充电宝,瞥见王川裹着外套鬼鬼祟祟从楼梯往下走,不知道去做什么。
我估算着时间,敲门进去问候。客人们休息得差不多了,王川还是没有回来。看见我进来,其中一个主任摆摆手,招呼一句,“咱不等他了,时间也晚了,回去吧。”
我合上包厢门,走到前台去结账,一边等他们换好衣服。
送走客人们之后,我站在足疗店门口,前台经理带着一个女技师一直站在我的身后。我想起王川的衣服还落在上面,不知道人跑到哪里去了,电话也不接。我转身回到楼上,经理和女技师依然跟着我。
我问她们,“账我结过了,还有什么事吗?”
经理支支吾吾地问我,“刚才,和你们一起来的那位先生,还没有回来吗?”
“不知道,他的衣服还在包厢里。”我说着,走回刚才的包厢,看见这俩人还隔着一米的距离跟在身后。我笑了,转向一直低着头的女技师,问她,“说吧,多少钱?”
“啊?”她小心翼翼地答,“什么多少钱?”
“他是不是告诉你,他下楼去换现金?”
这个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出头,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的小姑娘睁着圆圆的眼睛,犹豫着点点头。经理慌忙摆摆手,打岔道,“没有没有,您别误会,就是刚才那位先生把车钥匙落在卫生间了,我们想还给他。”
我笑着摇摇头,想来她是怕我举报他们,王川不敢转账,也是怕留下记录。这么久没有回来,应该是找不到商店换现金。“多少钱?”我又问了一遍,“我转给你。”
小女孩谨慎地瞥了一眼经理,见经理不说话,才吐出一句,“一千二。”
付完王川的嫖资,我躺在包厢的沙发上优哉游哉地等他回来。王川回来的时候,大概知道我已经帮他收拾利落了。他一声不吭地换好衣服,我们并排站在凌晨的街边等车。一辆空车闪着红灯过来,王川招招手,丢下一句,“我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。”
说完便上车了。
编辑:myxzm123 来源:黄金屋